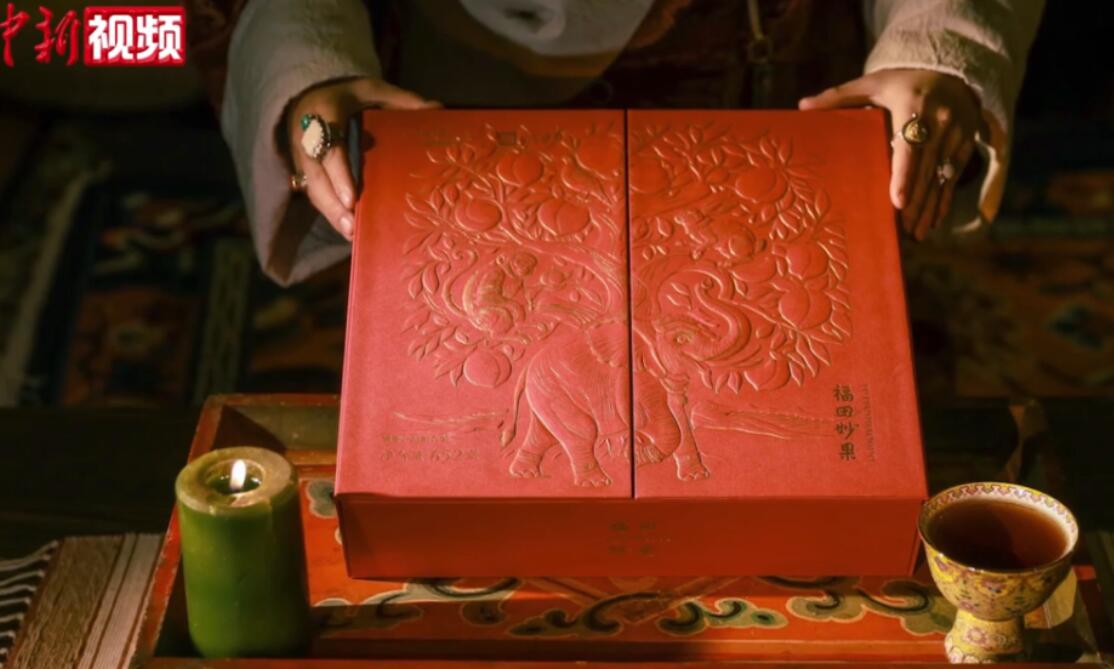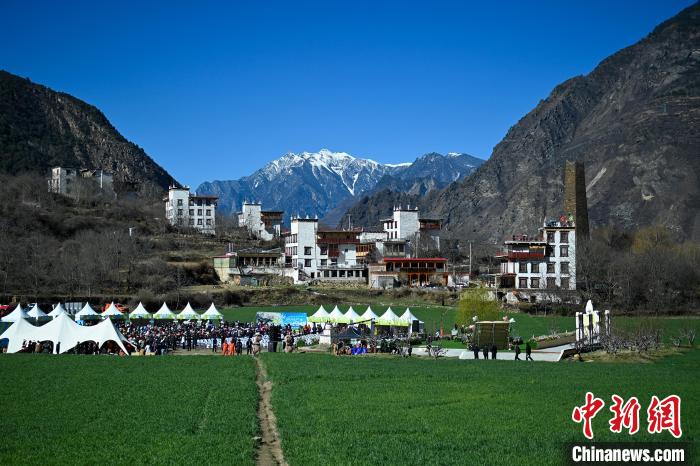作為長篇傳記文學《晏陽初》作者,當看到改編作品川劇《晏陽初》躍然舞臺時,心中滿是激動。晏陽初一生致力于“除文盲,做新民”偉大事業,被稱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和鄉村建設家。他所從事的事業具有長久的生命力,其平民教育思想與當今教育改革高度契合、鄉村建設理念與當前正在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高度契合,踐行讓人類共同富裕行為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契合,是近代少有的中國認可、歐美認可、第三世界認可的世界偉人,很有意思很有味道。川劇《晏陽初》用戲曲藝術的獨特魅力,將這位“東方圣哲”的教育理想與家國情懷展現得淋漓盡致,為觀眾呈現了一場兼具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文化視聽盛宴,不僅是對晏陽初精神的創新傳承,更是對家國情懷、人類大同理想的藝術禮贊。作為原著作者,內心深受觸動,讓我再次有了寫作的沖動。
一、主題宏大高遠:民族振興與人類大同的深情禮贊
“開腦礦”是晏陽初一生的理想和事業。在他眼里,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后,是民眾“腦礦”未開,認為教育可強民、民強則國盛,從而矢志“不做官,不發財,終身獻給勞苦大眾”,努力尋找一條不流血的強民救國之路。川劇《晏陽初》序幕就驚世駭俗提出要在“背二哥”中“開腦礦”,在“背二哥”的不理解中,喊出濟世新歌,“哪怕飛蛾撲火”,使晏陽初的偉大和悲壯躍然而出。
“平等”是晏陽初教育理念的精髓,也是他畢生的理想追求。他說“平民教育的‘平’字,是‘平等’意思;‘道德人格平等’‘受教育社會機會平等’”,進而治國平天下。他努力以平民教育為手段,培養民族新生命,塑造民族新人格,促進民族新發展。全劇將晏陽初“平等意識”貫穿始終,用唱詞來表達人物思想。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,自古以為讀書人就認為要高人一等。第一場戲《勸學》中,當王公遜欺負周長河不識字將稻谷借條的“二石”改為“二十石”還公然說人分三六九等時,喝“洋墨水”、學富五車的“晏陽初”卻堅決反對:“說什么天定把人分文野,說什么下等平民識字不可得;這都是騙人的把戲胡亂扯,全都是欺壓百姓的愚民策。晏陽初愿作平民教育苦行者,開民智喚醒雄獅東方白!”將晏陽初的平等理念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故事是推動情節發展最好的催化劑。作品用周長河借糧、抗日等故事來直觀展示教育對日常生活,促進個體命運、民族命運、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。
晏陽初一生尊崇“民為邦本,本固邦寧”的儒家思想,追求天下大同。他不分人種、不分民族、不分地域和國家開展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,足跡遍布世界,用思想和行動改變了數億貧苦民眾的命運。在接受美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采訪時說到,“我要向全世界提出這一個問題,請求解答。為什么不能團結所有國家、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——愚昧、貧困、疾病和腐敗政府呢?”尾聲中,晏陽初的理念得到國際推廣,他與孔子的對話表達了對人類共命運與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,將全劇主題升華至哲學高度。在世界格局深刻變革、全球化飛速發展的今天,如何超越國界、民族和種族的界限,實現人類的共同進步與和諧共處,是我們不得不思考和面對的問題。正如新華社撰文評論《晏陽初》一書所說:“有意味的《晏陽初》,講好了屬于民族、人類、未來的中國故事。”
二、架構匠心獨具:線形敘事與精神意象的科學重構
川劇《晏陽初》以“天問”為始、“定魂”為終,中間六場戲分別聚焦晏陽初的開展識字教育、生計教育、衛生教育、歸鄉看母、守志、抗戰等核心事件,層層遞進,構成“勸學—種子—迎新—回家—守心—哭瓷”的意象鏈,清晰展現了晏陽初從開展平民教育到晚年堅守的人生軌跡。敘事結構精妙,既遵循傳統戲曲的線性邏輯,又通過象征符號反復強化主題,賦予全劇濃厚的象征意蘊。
全劇采用傳統戲曲的線性敘事,層次豐富、脈絡清晰、邏輯嚴密。例如第一場“勸學”中,鄉紳王公遜偽造借據剝削文盲農民周長河,直接指向“愚”與“私”的社會癥結,不僅展現了當時社會底層人民因無知而遭受的苦難,也直接揭示了晏陽初開展平民教育的緊迫性。第三場“迎新”通過救援難產婦女的生死危機,展現衛生教育推廣時面臨的困難以及救死扶傷的重大作用。第六場“哭瓷”借抗戰背景下定縣淪陷的悲劇,將個人理想升華為民族精神的吶喊。這些沖突不僅是情節推進的引擎,更是晏陽初教育理念的實踐注腳。
戲劇進行了大量的精神意象重構,較好展現了人物思想,升華了主題。首先,將“瓷器”作為核心意象貫穿全劇。瓷器和中國的英文單詞都是china,戲曲巧妙的運用了這一意象。定瓷創燒于隋,發展于唐,興盛于宋,是中國五大名窖之一,在中外陶瓷史上占有特殊位置,可以說是定縣的代名詞。定縣實驗中,定瓷是平民智慧的結晶;抗戰犧牲時,它是民族精神的化身;尾聲中,它又升華為人類大同的象征。這一意象的層層遞進,將個人敘事升華為民族精神。其次,大量運用對比聯想。比如,序幕中巴山背二哥的號子與晏陽初的獨白形成時空對話,寓意著平民教育“開腦礦”與傳統勞作“開金礦”“開銀礦”的精神碰撞;“路不平”這一農民角色雖然在實際中并不存在,但他代表的卻是千百萬被“開腦礦”后底層民眾,具有深遠的象征意義。再次,通過象征符號的反復強化主題。比如,舞臺布景中,如大巴山的懸崖峭壁、定州開元寺塔的布景,既營造了場景氛圍,又暗喻教育理念的傳播與扎根。“守心”一場中運用意識流手法呈現農民識字、棉花豐收的幻境,突破了傳統戲曲寫實的框架,為觀眾帶來全新的審美體驗。
三、人物形象豐滿:理想主義與時代洪流的深刻塑造
川劇《晏陽初》充分運用幫腔、韻白、唱詞等形式,塑造了形象鮮明、立體的人物形象,每一個角色都被賦予了獨特的性格和豐富的情感,共同構成了一個生動的時代群像。
晏陽初的形象塑造無疑是核心。川劇通過“教育家”“丈夫”“游子”“戰士”等多重身份的刻畫,呈現了一個知行合一、立體而真實的平民教育家,展現出他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偉大的人格魅力。他的唱詞充滿理想主義色彩,“我要用平民教育去沉疴,我要讓仁愛展長河”,彰顯了他以教育濟世的崇高情懷。在面對經費短缺、手術風險等現實困境時,他的抉擇展現出務實精神,如在“迎新”中為產婦簽字進行剖腹手術,承擔巨大風險卻毫不退縮。在“哭瓷”一場,他將張瓷娃犧牲前送的瓷杯與“china(中華)”聯系起來,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,完成了從教育家到民族精神象征的升華。
配角也栩栩如生、各具特色。傅葆琛、馮銳、陳志潛等平教會同仁,他們各自代表著無數平民教育運動的參與者和奉獻者。傅葆琛的沉穩、馮銳的執著、陳志潛的醫者仁心,相互映襯,展現出知識分子為平民教育事業共同奮斗的精神風貌,共同構成知識分子的精神圖譜。許雅麗作為晏陽初的妻子,她溫柔堅韌,不僅在生活上給予晏陽初支持,更在理想上與他志同道合,她的唱段“同理想同抱負生死相依,一條路一顆心雙飛蝴蝶”,既是愛情宣言,也是志業共鳴,展現了夫妻間深厚的感情和對平民教育事業的共同追求。王公遜與周長河則形成鮮明對比,王公遜從自私自利的剝削鄉紳轉變為抗日烈士,周長河從文盲農民成長為識字新民,他們的轉變過程生動地體現了晏陽初“除文盲,做新民”教育理念的實踐成果。
四、藝術獨具特色:川劇韻味與現代審美的完美融合
川劇作為一種傳統藝術形式,能夠與現代題材相結合,本來就是一種創新。同時,劇中的對話、唱段、舞臺設計等都充滿了創新元素,既保留了川劇的獨有韻味,又融入了現代審美元素,賦予了作品新的生命力,整臺劇既具有歷史厚重感,又充滿時代氣息。這種藝術形式的創新表達,為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,也讓我看到了傳統藝術在新時代的無限可能。
文學性與地域特色兼具的唱詞與韻白是該劇的一大亮點。唱詞中既有“寧為瓷器不為瓦,生生死死也英雄”這樣富有詩意且氣勢磅礴的“飛句”;又有王公遜的市井俚語“格老子”“裝蟒吃象”,以及晏母的巴中方言,生動地展現了人物性格,強化了地域文化特色。這些唱詞和韻白在推動劇情發展的同時,也讓觀眾感受到川劇獨特的語言魅力。
演員們的表演生動傳神,將角色內心的情感通過精湛的技藝展現得淋漓盡致。他們的一招一式、一顰一笑都經過精心設計,動作與情感緊密結合。晏陽初在“守心”中鼓勵團隊時,堅定的眼神、激昂的言辭以及有力的手勢,充分展現出他的領袖風范和堅定信念;在“哭瓷”中,晏陽初得知定縣淪陷、平教會成員犧牲時的悲痛欲絕,通過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的細膩演繹,讓觀眾感同身受。
音樂與舞蹈在劇中也發揮了重要的敘事功能。大巴山背二哥的號子、定縣田野的勞作歌舞、抗戰場景的槍炮音效等,共同構建了立體多層次的聲音景觀。“背二歌”與“平民千字課”朗誦的并置,象征著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教育理念的沖突與融合。音樂的節奏和旋律隨著劇情的發展而變化,時而激昂振奮,如晏陽初演講時的音樂,展現他的壯志豪情;時而舒緩溫情,如晏陽初與家人團聚時的音樂,烘托出親情的溫暖,增強了劇情的感染力。
總之,川劇《晏陽初》用川劇的獨特的藝術形式,塑造了晏陽初的平民教育的偉大實踐和濃厚的家國情懷,與原著的思想高度契合,展現一個可信、可敬、可愛的中國形象,是一部成功的藝術作品,是對先生精神的創新表達和時代詮釋,是向世界遞上的中國名片。
川劇又稱川戲,晏陽初是川人,川劇是曾是他的最愛,小時候時常流連在巴城龍母宮看川劇,在他《九十自述》中就有提及,只是沒想到一百多年后他自己竟然也成為川劇的主人公。我想,先生若是泉下有知,也定會欣喜萬分。謝謝川劇《晏陽初》的時代創新表達和舞臺演繹,讓我們再次看到了先生的榮光與偉岸。(作者苗勇系知名作家、四川省總工會副主席)